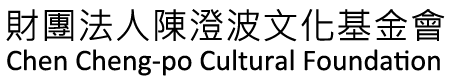之前連續兩週的專欄文中,我們先是介紹了戰前日本內地藝術家們對日本「地方色彩」(或可說國族色彩)的投入,之後是介紹表現中國「地方色彩」的投入,對照陳澄波的美術明信片收藏,可以發現日本同儕這些投入,對於彼時的台灣藝術家的在地繪畫是有所啟發的,他們看到了洋畫的日本化過程,或是表現中國風景的手法,成為思考台灣「地方色彩」最好的他山之石。
收藏中,中野和高的《其樂融融的一家》(1928第九回帝展 , 圖1)幾乎可斷定是發想自法國印象派藝術家Frédéric Bazille的名作《家庭團聚》(1867-68 , 圖2),而李石樵《楊肇嘉氏之家族》(1936 文部省美術展覽會 , 圖3)也透露了雷同的氣氛:三幅畫人物均刻意擺佈到有些彆扭。中野和高的作品儘管與Frédéric Bazille的名作很像,但有其「地方色彩」的轉化,而李石樵的「地方色彩」則更加濃郁:色溫、風景及衣飾使人一眼即知該畫的台灣出身。



我們還可以從陳澄波其他明信片收藏裏去找出許多日台兩地「地方色彩」相互輝映的趣味,比如李石樵的《編物》(1935第一回二部會美術展覽會 , 圖4)與鈴木誠 《看畫的女人》( 1940第五回新制作派協會展覽會,圖5)同樣是處理二個坐著的女人,但色彩編排卻很不一樣,台灣版是較偏暖色系加高彩度,日本版則是較偏寒色系加低彩度。這樣的對立是常見的。


這樣的差異僅是風土之別嗎?似乎不是,因為同樣是以台灣題材來詮釋台灣的「地方色彩」,台日藝術家仍走上不同的路線。以下述三件作品為例—-川島理一郎的《臺灣歌妓(之一)》(1933第八回國畫會美術展覽會 , 圖6)、李石樵《在畫室》( 1934第十五回帝展,圖7)以及李梅樹 《紅衣》 (1939第三回文部省美術展覽會 ,圖8)—-,都描繪台灣年輕女性肖像,但差異很明顯:首先,台灣藝術家們偏好選擇以摩登氣息出場:洋服、歐式家具、地毯、玻璃酒杯、窗外的洋樓等等,日本藝術家偏好描繪一種明顯異於日本與西方的台灣:台灣傳統服飾、大花的壁紙圖案、傳統樂器、木刻家具等等。其次,在美感語言運用上,台灣藝術家努力營造一種古典沈靜的人物畫氛圍:強調對稱的構圖、直線線條的使用等等;相對地,日本畫家畫面中宛如Henri Matisse(馬諦斯)的曲線應用與圖案設計,使得畫面頗為活潑奔放。


第十五回帝展,1934(陳澄波藏)

類似的案例,小澤秋成的《高雄風景(其二)》(1933第二十回二科美術 展覽會 , 圖9)將高雄畫出日本內地看不到的那種刺痛肌膚的熱度:地面烈日下的陰影、有著感覺已被晒枯部份樹葉的椰樹以及撐著洋傘的行人等等,這是日本人所詮釋充滿南國熱度的台灣地景。很巧地,小澤秋成這種熱力四放的樹木描繪,出現在六十多年後台灣畫家李俊賢的作品 :《南島風光-金蕉園》(1996, 圖10)。


然而,熾熱的氣候很少是戰前台灣藝術家的強調重點,以陳澄波的風景畫作為例,《嘉義中央噴水池》(1933, 圖11)同樣有著晴空萬里的天氣,但地面陰影並不像小澤秋成作品那麼深色、那樣黑白對比明顯,自然,視覺溫度降低許多。再一例,陳澄波的《椰林》(1938, 圖12)與小澤秋成的《高雄風景(其二)》描繪了同樣的植物,但前者並沒有樹葉枯黑感,也沒有毒辣烈日才會出現的影子,使得陳澄波筆下的椰林讓人感覺舒服許多。


日本人筆下的台灣,除了表現出「非常異於日本」,少許案例是畫出「另一個日本」,亦即「地方色彩」方面的表達能力或意志是可質疑的,日本內地藝術家佐佐木栗軒的作品《黃昏(披星戴月)》(1931第五回臺展, 圖13)即是一例,明明從衣著、建築到水牛都意指台灣,但卻是以和式美感框架起來:從構圖、用色、建物過斜的屋頂(寒帶下雪地區的建物特色)以及東亞(中、日、韓)傳統畫演繹老松樹的手法等等,讓人會誤以為這是一張描繪日本內地的雪國風景畫。這個趣味,雷同於席德進那些經常將台灣畫成「另一個中國」的風景畫(圖14)。相反地,在台灣戰前藝術家的風景畫作裏,我們很難能發現將異地(日本或中國)畫成「另一個台灣」的作品。


一幅作品的「地方色彩」是由三個向度相乘的結果:眼前風土、藝術家出身、表達能力或意志,圍繞著台灣島作為討論核心,本文先是比較「日本人畫的日本」以及「台灣人畫的台灣」,接著比較「日本人畫的台灣」以及「台灣人畫的台灣」,最後是處理「表達能力或意志」;從中,我們理解到戰前的台灣藝術家並不跟隨日本人的視角去領略地方色彩,而是紮實地內化了地方色彩的相關方法學,從中發展出自我觀看台灣的(集體)路線;才剛接觸洋畫的第一個世代即有這樣的能力與堅持是很令人驚訝的,被殖意識或許是達成這項成就潛在的推動力:畫出不同於日本的台灣、畫出不同於日本人畫的台灣、畫出摩登的台灣、畫出樂土般的台灣……這批菁英很明顯要開創出自己的路,而在美術的世界埋下國族美感的種子。
本專欄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 藝術社會學博士,這個系列文章的研究樣本來自陳澄波基金會策畫與出版的《陳澄波全集》第七至九卷。